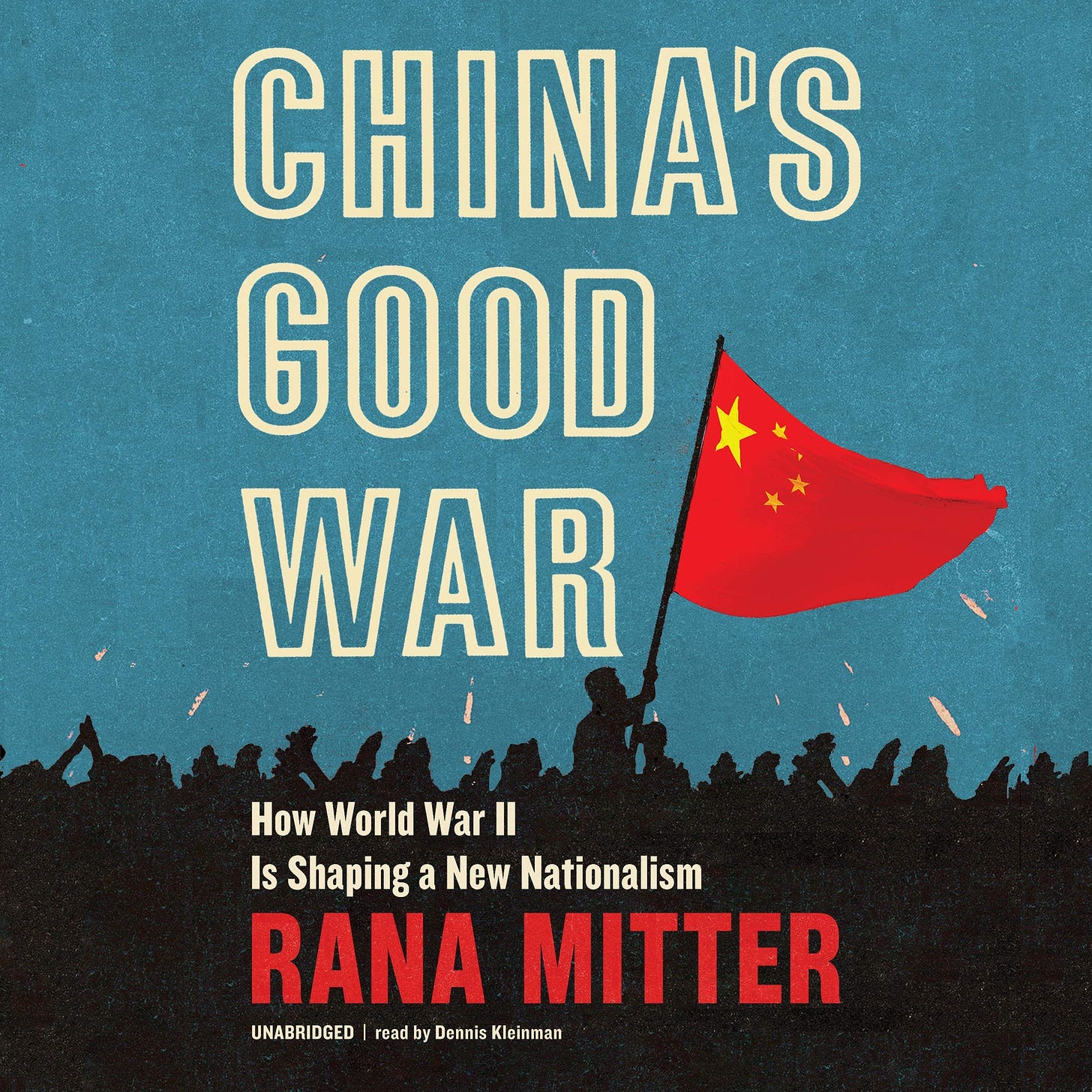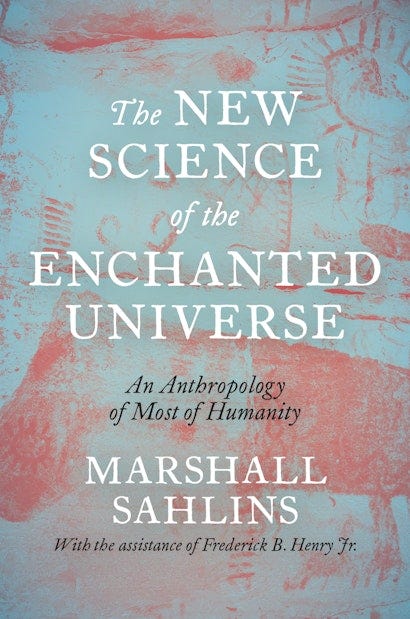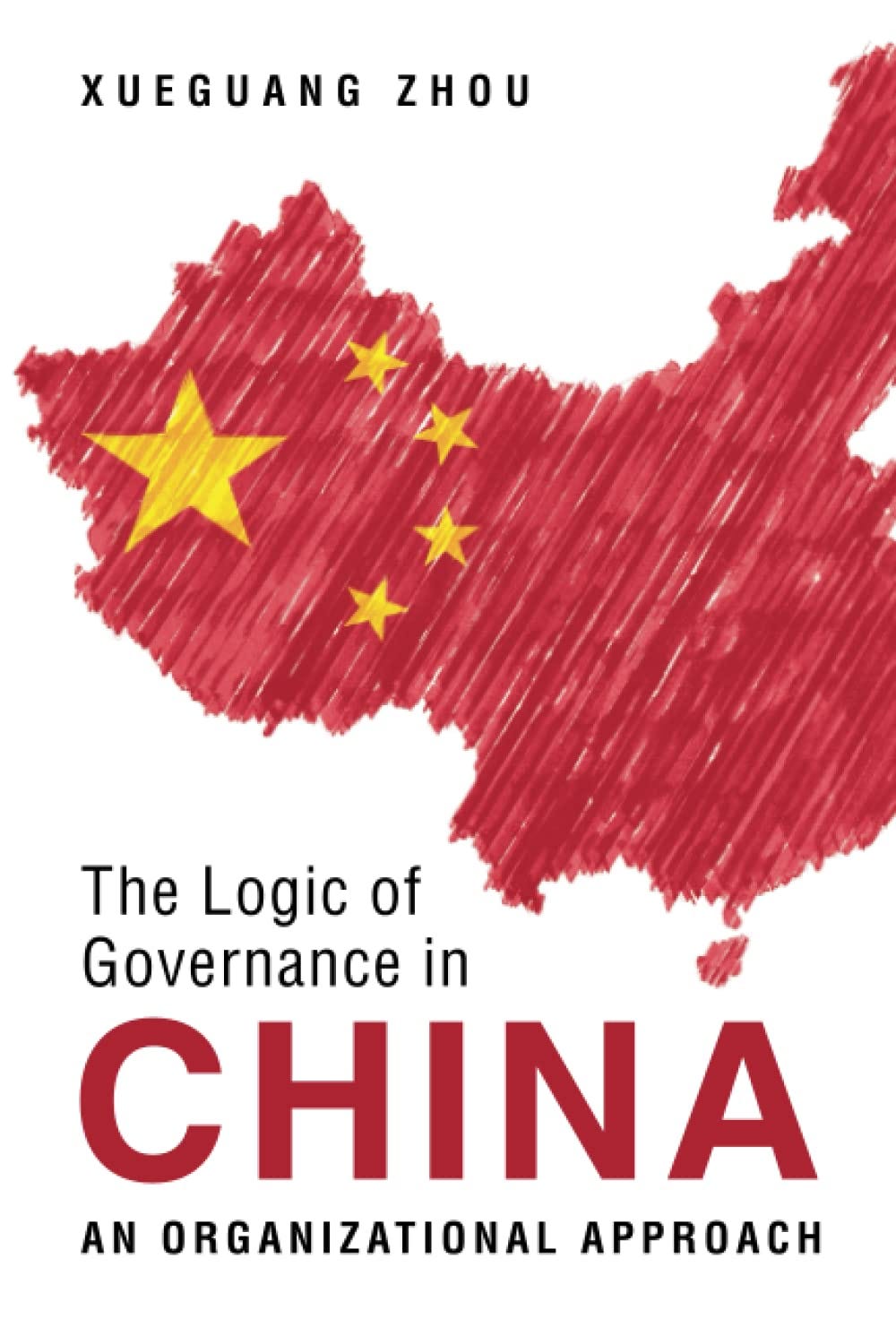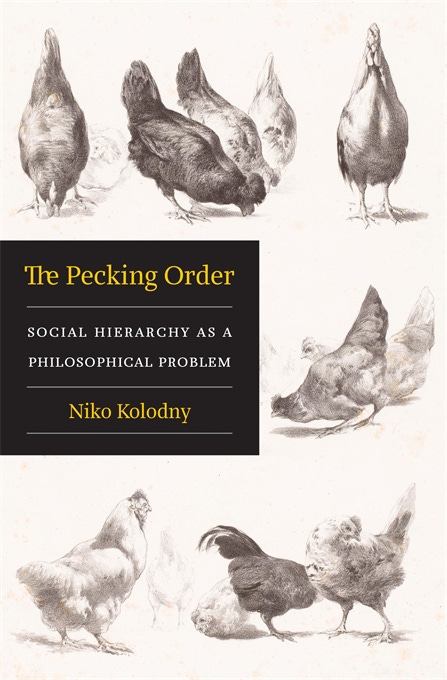當我們說政治社會的時候,我們首先預設的是一個制度化的社會現實。所謂制度化就是對自由的管理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社會秩序。但制度化并不總是成功的,而且不同的社會形態將優先順序放在不同的事務上。比如有的國家借由政治運動或歷史情結來補足制度化缺陷,有的國家則進展到用修復社會等級體系來剋服制度化的副產品。甚至於連沒有社會結構、純然平等主義、完全一盤散沙的原始部落,也並不與社會等級和制度化完全絕緣。這些都是怎麽做到的呢?
近幾年,社會科學各個領域都在不斷攻城略地,新出版物應接不暇。以下我們從近五年新出版圖書精心挑選出五種,來嘗試窺探社會科學在以上研究領域新的動向。
在這個書單裏,你會看見因爲恐懼抓捕只好躲進監獄避難的敘利亞人、患上“開羅綜合徵”的中國人、毫無社會組織卻仍能形成秩序和規範的原始部落、依靠政治運動來彌補制度性缺陷的新威權主義國家、以及努力剋服社會等級體系的民主國家。
從這些選題可以看出,本書單的甄選標準是主要依照趣味性、知識性和學術價值并重的原則,同時也兼顧公衆所能接受的通俗程度。
1. Lisa Wedeen: Authoritarian Apprehensions (2019)
敘利亞一個小村子,有天收到上峰命令:不許村民給官員拍馬屁。這個命令給當地村民造成極大困擾,因爲他們此前一直習慣了給官員拍馬屁。這讓村民們感到很焦慮,人們搞不懂這個命令到底是要圖什麽:如果不能自由地拍官員馬屁了,還是人過的日子嗎?村民們既要爲怕馬屁擔驚受怕,又要爲不拍馬屁承擔難以想象的後果,於是想出來一個絕妙主意:主動投案自首,把自己關進監獄裏,這樣就不用爲拍馬屁或者不拍馬屁承擔風險了……
這是一個虛構故事,來自敘利亞2010年一檔情景喜劇,當年這個劇一度引起萬人空巷,造成轟動。像這種含有政治諷刺色彩的喜劇,在巴夏爾·阿塞德(Bashar al-Assad)執政前十年並不少見,許多都能造成轟動效應。你也許覺得在一個威權主義國家,能有空間留給政治諷刺喜劇,一定是相對開明吧?也許還有許多中國人產生共鳴,尤其是看過1990年代到2000年代初春晚小品的人,可能感慨當時的政治諷刺既露骨又大膽,就覺得那20年風氣還是相對開放的。當然,這些都只是未經批判的直觀感受而已。
經過數十年扎根敘利亞的田野調查,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家 Lisa Wedeen 發現,在敘利亞這樣的專制國家,即使政治喜劇,也可能悖論性地支持跟配合國家的規訓機制,也就是説,可能有意無意地製造服從威權專制的效果。對喜劇來説,專制政府所容許的“大不敬”(irreverence)事實上也在遏制或轉化其感受到的敵意——有時候,這種敵意還是故意誘導和鼓勵的結果,有點像中國央視主旋律電視劇《以人民的名義》故意誘導民衆對“腐敗官員”產生敵意——這樣的喜劇給人一種風氣開明的錯覺,并且强化公民對專制政府的依附和服從。
更進一步,Lisa Wedeen 就開始逐步深入探討專制社會普遍存在的一種社會現象,簡單説來就是:“我明知道這樣做不對,但是……”——這裏的“但是”就顯得意味深長了,因爲很多情況下,由“但是”引導出來的意見,通常悖論性地抗拒我們自身的意願——由“我明知道這樣做不對”所暗示的意願。
Lisa Wedeen 將這種情況稱爲“曖昧性”(ambivalence),它顯示出一種在依附於現有秩序和渴望變革之間的矛盾糾結心理。更重要的是,這位政治學家從敘利亞田野調查中進一步推進和發展了意識形態理論——她認爲“意識形態”(ideology)恰恰就是在日常生活實踐中,通常沒頭沒尾地表達出來的,體現情感依附的具體行爲和話語。意識形態不止存在於政府支持者那裏,在中間派和反對派之間也普遍存在。意識形態呈現出來的矛盾和焦慮特質,很好地體現在上述“曖昧性”之中。
這個新的意識形態概念是 Lisa Wedeen 對其在1999年提出“象徵性的規訓權力”的進一步發展。在《統治的模糊性》(The Ambiguities of Domination, 1999/2015)中,Lisa Wedeen 發現,敘利亞專制政府旨在通過大肆推動對時任總統哈菲茲·阿薩德(Hafez al-Assad,現任敘利亞總統巴夏爾·阿塞德的父親)的個人崇拜,製造服從(compliance)。也就是說,敘利亞專制政府的統治策略是基於服從而不是基於合法性(legitimacy):專制政權通過强迫民衆參與針對獨裁者的致敬儀式來製造服從,即便參與者和發起者都不相信政府的虛假宣傳,服從仍然產生了——服從的具體形式,就是官僚和平民行爲擧止“好像”(“as if”這個概念對 Lisa Wedeen 很重要)表現出對領袖的敬拜。這種“好像”政治(a politics of “as if”)看上去既不理性,又虛僞透頂,但是非常有效地製造了服從,因爲只有言語和行爲上表演服從,才能實現權力實體化(to substantiate rather than legitimate power)。
這種情況在中國同樣存在——中國重新興起對國家領導人的個人崇拜,很大程度上也是爲了强化服從,而不是爲了塑造領導人的合法性。這種服從形式,不但體現在上至官僚下至平民針對習近平本人的“學習”活動、“學習”會議、“學習”報告、“學習”語錄、“學習强國”軟體等一系列活動,也體現在習近平語錄和形象廣汎存在於中國社會每個角落。即便對習近平本人不滿、或者不相信官方宣傳的人,在公開場合仍然表現出服從。很多時候,個人加强自我審查(包括網民規避網絡審查)也是一種服從形式。
本書精彩跌出的田野調查案例和分析,及其敏銳的洞察力和發人深省的深描,對比照和瞭解中國的社會現象和專制主義制度有深刻藉鑒意義。值得一提的是,本書作者故意采用“Authoritarian Apprehensions”命名本書,主要基於“apprehension”一詞三重意思:抓捕、憂慮和理解。本書也正是圍繞這三重意思來展開。另外,從前面提到的《統治的模糊性》(1999/2015)一書可以看出,Lisa Wedeen 深受象徵派人類學家 Clifford Geertz 影響,她的理論大廈根基就是從象徵人類學開始的。
2. Rana Mitter: China’s Good War (2020).
牛津大學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 Rana Mitter 在本書裏提出了一個概念:“開羅綜合徵”(Cairo Syndrome)。這個概念指的是中國不斷通過回顧二戰(也就是中國的抗日戰爭史)和戰後時期來塑造道德制高點和增加自己(以及盡可能削弱日本)在戰後國際秩序中的發言權。
這個“開羅綜合徵”得名於1943年的“開羅會議”。“開羅會議”在西方世界看來,并沒有多特別的重要性,但是在中國跟台灣,看起來情況似乎并不是這樣。2013年,全世界只有中國跟台灣舉行了“開羅會議70周年紀念”。到2015年中國的主旋律電影《開羅宣言》才假托美國羅斯福總統之口,道出中國想要成爲“負責任的世界大國”的自我定位。
這種沉浸於二戰史的民族狂熱,給人一種感覺,就好像中國一直沒有走出戰後時期——或者説,中國的戰後時期太過於漫長。同盟國和軸心國多少都經歷了艱難的戰後重建,但是中國沒有經歷過。因爲在1945年二戰結束以後,緊跟著1946年中國就爆發了内戰,内戰結束後中國又經歷了長達三十多年社會動蕩。1949年以後,在忙於共產主義革命的前三十年裏,有關抗日戰爭的集體記憶通常只限於官方紀念活動或者用於歌頌共產黨的樣板戲表演,在民間這類集體記憶遠遠不像1982年以後那樣强烈。
1982年似乎是一個轉折點。在長達三十多年共產主義動亂告一段落之後,中國剛剛開啓改革開放。這時候共產主義信仰開始出現危機,并且在那以後再沒有一種意識形態足以比肩共產主義來凝聚人心。這一年中日建交才10年,而且正在大力支持中國改革開放。但是也在這一年,日本修改教科書引起了爭議,給中國提供了一個通過塑造民族主義來重新凝聚人心的藉口。從那以後,中國就開始越來越沉迷於二戰敘事,不但在國内大肆宣揚修正主義歷史觀、推動奠基於這種歷史觀的所謂“愛國主義教育”,還在國際交往中頻頻重申領土訴求以及中國作爲二戰戰勝國的國際地位。
Rana Mitter 注意到,中國遲遲不肯走出二戰歷史可能由多種因素造成。一是有關抗日戰爭(但事實上是修改過)的集體記憶被用來重塑中國的政治文化。尤其是在不以階級鬥爭爲綱之後,抗日戰爭史被用來塑造一種新的民族主義和改造民族認同。其次是中國借由抗日戰爭將本民族描繪成占據道德制高點的强大戰勝國。到習近平時代,抗日戰爭仍然被當作中國近代反抗侵略史中一次完全的勝利來紀念。第三點也與這個企圖有關:中國希望通過不斷重申戰勝國地位和道德制高點,來攫取更重要的國際發言權和更高的國際地位。第四點與第三點也息息相關:中國的國際關係就是由跟二戰史有關的觀念來形塑的。中國具體是怎麽做的?
本書對於深度分析中國社會的反日現象,追溯中國的二戰史修正主義觀念之形成,對於中日關係研究有重要啓發意義。比如在作者看來,中日關係最好不要理解成衝突關係,而是要將這種關係,納入到中國有關自身民族認同本質持續爭論之中來看。這裏又回到開頭的話題:中國爲什麽這麽在乎“開羅會議”?本書作者認爲,這關係到中國是否能夠重新接續1930-1940年代未完成的民族性改造。
本書曾榮獲2021年“亞洲研究圖書獎”(ICAS Book Prize)。但是不可否認該書缺陷也相當明顯。比如這項研究建立在這樣一個假設之上:中國重新融入國際秩序并不對國際秩序構成挑戰。與此同時,作者也沒有解釋爲什麽中國會采納二戰歷史話語來重塑民族認同和民族主義。另外值得探討的話題是:中國這種修正主義歷史觀對於中國如何感知和認識戰後國際秩序有什麽影響?
3. Marshall Sahlins: The New Science of the Enchanted Universe (2022)
本書是芝加哥大學人類學家 Marshall Sahlins 最後一部力作。中文讀者知道 Marshall Sahlins,通常是因爲《歷史隱喻與神話現實》(Historical metaphors and mythical realities, 1981)、《歷史之島》(Islands of History, 1985)跟著名論文《甜蜜的悲哀》(The Sadness of Sweetness, 1996)。通過這位人類學家化腐朽為神奇的精湛技藝,許多讀者都記住了庫克船長(Captain James Cook)在被夏威夷原住民殺死後是如何被煮得香噴噴的。
Marshall Sahlins 所關心課題與其寫作一樣,一如既往地吸引讀者。這位極富創造力的人類學家到晚年開始思考一門新科學,不管是對人類學,還是對政治學和哲學,都有著極大啓發性。這門新科學是圍繞一種“宇宙城邦制”(cosmopoliteia)假説來進行的。
Marshall Sahlins 深入考察了大量民族志、考古學、歷史學、政治學、哲學、社會學、神學和神話學文獻,他發現,人類歷史上絕大部分文化都將超自然力量(神、鬼、妖、精靈和半獸人或半神人等等)看成是真實的人或者“元人”(metapersons),看成是與人類互動并且操控人類命運的宇宙社會的一員。也就是説,這些“元人”并不是哲學意義上的先驗概念,而是内在於經驗中的真實概念。這種概念對康德主義來説是顛覆性的,因爲這些作爲“物自體”(Ding an sich)的“元人”,不但是可知的(knowable),還是與人類社會互動的(sociable)。這些“元人”是某種高級人類形態,而宇宙社會就是由這種種高級人類形態與人類存在共同構成的等級社會,人類社會不過是這個等級社會的小小的一部分。
這個“宇宙城邦制”假説可以表述爲:人類社會并非是複刻超越於其上的某種神聖秩序,而是這種神聖秩序的延伸,并且自身也構成了這個秩序的一部分。
Marshall Sahlins 發現,即使在組織程度最低、最缺乏等級體系的部落社會,也有賴於依靠一個經過等級化組織的宇宙社會(a hierarchically organized, cosmic polity),在這種社會底下,人處於依附地位,人對這個社會心心念念,表現恭順,并且知道自己是處於弱勢,易受傷害。比如生活在北極圈的Naskapi人,將血喙蝇(moose-fly)看成是管理魚類和 Naskapi 族的主人,Naskapi 漁民能不能捕到漁獲(或者捕到什麽漁獲),取決於漁民有多順從於掌管漁業的靈力(spirit-power)。但 Naskapi人 是毫無社會組織的,也沒有所謂權威存在,他們只知順從於來自靈力的統治力量,因爲是靈力保障他們的生存條件:如果他們在捕魚技術上有所成效,全賴於他們與漁獲主宰者的關係。
又比如亞馬遜河流域的 Achuar 人,他們主要依靠捕獵和最原始的刀耕火種爲生。其社會組織程度接近於零,沒有酋長,沒有村莊和社群,也沒有母系或父系氏族。但是這并不意味著 Achuar 人是沒有社會制度或社會形態的。管理獵物的“獵獲之母”(game mothers)同樣掌管著 Achuar 人的社會秩序,因爲狩獵行動須得與“獵獲之母”協議之後才能取得效果。這個“獵獲之母”就像是個“大號的人”(an outsized personage),所有狩獵對象(game-persons)——也被認爲是“人”——都處在“獵獲之母”的權威之下,由她根據與獵人的協議來分配和決定最終獵獲。對於 Achuar 婦女來説,木薯和其他農作物之母 Nunkui 女神,也是某種制度或法則的化身。婦女通過一套複雜的聲音、隱喻和服從姿態,用符咒來將自己變成 Nunkui 的化身,將農作物作爲自己孩子來養育。
有鑒於這一特點,我們的人類學家說:人并不是憑空創造了神,而是將已經作爲其生存條件的力量視爲現實。人并沒有想象神,而是將超出人的力量客體化和主體化,而他們自己有賴於依靠這種力量生老病死。正因如此,Marshall Sahlins 說,大部分人類歷史和社會形態都表明,人的存在已經是他律化的結果(human existence…has been heteronomous)。
Marshall Sahlins 的“元人”概念似乎在超自然力量跟構成超自然秩序的規范性法則之間猶豫不決。對政治哲學來説,“元人”像是一種超出人類社會、破除人類中心主義迷信的制度性規範,像是人與自然秩序協商的結果,既不是純然專斷的,也不是純然被動的。而“宇宙城邦制”假説顯然將研究觸角,進一步推進到“政治人類學”或“政治神學”領域,也許這就是 Marshall Sahlins 最後想象的新科學。
這本書同時也引起我們思考,構成我們知識主體的歷史性經驗是如何構成制度性現實和政治社會的。可以説,Marshall Sahlins 的探索和提出一系列遺留問題,對政治和政治社會如何形成構成了新的挑戰,因爲在無政府狀態下的人類社會,仍可能是制度化的,即使這樣的社會毫無組織可言。政治再一次成了巨大的謎題。
中文讀者比較少知道的是這位人類學家還專門研究過中國的孔子學院,並發表過《孔子學院:惡意學術插件》(Confucius Institute: Academic Malware, 2015)來表達强烈反對意見(這本書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美國針對孔子學院的遏制性政策)。
4. Zhou Xueguang: The Logic of Governance in China (2022)
本書作者是斯坦福大學政治學家周雪光教授,該書中文版《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出版於2017年,但是因爲衆所周知的原因遭到北京當局下架,也不再重印。但本書英文版與中文版内容上存在很大不同,大部分材料都有重新修改和重寫,期間作者的思想也發生了較大變化,可以説與中文版是兩本書了。
本書的思想雛形可以追溯到2015年的論文《從黃宗羲定律到帝國的邏輯:中國國家治理邏輯的歷史綫索》,該文提出,中華帝國的國家治理邏輯是:通過在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之間和在(中央)象徵性權力跟(地方)實質性權力之間找平衡,來剋服帝國國家治理的“委托-代理”難題。
到本書英文版,周雪光將關注重心放在中央集權與實質性地方治理之間的“基礎性緊張關係”(the fundamental tension)上。爲剋服這種基礎性緊張關係,中國歷史上出現了四種反應機制:一是基於穩定的制度安排,在中央政策與地方執行之間出現可變結合;二是穩定但有彈性非正式制度與正式制度共存,并補充正式制度;三是政治措辭和官方意識形態的儀式化,在維持地方官員象徵性服從和保障央地權威在實踐上的鬆散結合上發揮的重要作用;四是由上而下的政治運動(top-down campaign-style mobilization)被中央政府用來加强中央權威,重新劃定地方靈活性的邊界,以及加强央地權威的可變結合。
由於應對“基礎性緊張關係”的制度性安排自身存在的局限性,中國在向法治和官僚體制理性化進行制度轉型的過程中遭遇了巨大困難。不同於基於法律和理性合法化的韋伯式官僚系統的特點,中國官僚體制往往受制於中央政府任意專斷的權力。因爲法治、官僚體制理性化、專業化等新制度跟新機制傾向於削弱中央權威,催生出地方自主和多中心管理模式,這被認爲對集中中央權威和對上級權威任意專斷地干預地方構成威脅。與此同時,法治和官僚體制理性化有促成不同地區推行標準化實踐的傾向,這就會大大減損地方政府靈活貫徹中央政策的執行力,降低地方治理的效力。
這種現象并不是當代中國特有問題,而是歷史上就存在。以清代乾隆朝“叫魂”案爲例,1768年由“叫魂”巫術引發的恐慌,迅速從中國南方傳到華北地區,引起朝廷震動。皇帝認爲這種現象是造反的幌子,地方政府不得不用掩蓋事情真相來逃避責任。於是皇帝就發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調動各級官員追究造反頭目並嚴懲逃避責任的官員,結果很多官員就因爲涉嫌謀反和逃避責任遭到嚴懲。但是到年底時才發現,根本不存在所謂造反證據,連密謀造反的證據也沒找到。皇帝只好叫停了政治運動,象徵性抓幾個高官當替罪羊。這種情況在中國歷史上絕不少見。由習近平發起的反腐運動也是這樣。本來中國有公檢法系統來懲治腐敗問題,但不管是習近平的中央紀檢委,還是其前任的中央政法委,都成了超越常規法律程序之上的反腐手段。但習近平反腐運動不但達到了運動規模,還大大强化了中央集權。不但如此,習近平時代湧現的“扶貧運動”、“餐桌革命”、“厠所革命”、“垃圾革命”……全是由中央直接發起的、直接干預到地方和個人的政治運動,本質上與乾隆皇帝發起的追究“叫魂”案運動如出一轍。
周雪光說,中國歷史上絕大部分時間都奉行這種靈活、鬆散的制度性實踐。雖然表面上看起來靈活性和適應性似乎是制度化社會的有益補充,但是其代價也非常明顯,尤其是效率低下而且自身缺乏穩定性。
這種不穩定的央地緊張關係既是社會動蕩的根源,也是造成改朝換代頻繁的重要原因。最重要的是,這種不穩定的制度缺陷實際上有反制度化或者抵制制度化的傾向。在這種制度之下,官僚體制的理性化和常規化進程,總是遭到中央政府用任意而且專斷的權威打亂。由於缺乏可依賴的法律制度同時規範和約束中央和地方權力,中國官僚系統内部也與中國社會一樣,將“關係”視爲減少阻力、規避風險和繞開常規法律程序的重要手段之一。在這種政治生態中,結黨營私和系統性腐敗現象是無法根治的,而且中央與地方互不信任還加深了自身的不安全感。這種情況使得中國歷史像遵循某個周期一樣循環。
5. Niko Kolodny: The Pecking Order (2023)
John Rawls 在其名著《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 1971)中遺留下來一些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第一,個體享有的自由權利應與其他人的同等權利相容,但是也存在不懂得如何運用自由權利的情況。這時候政府如果跳出來以“爲你好”的名義干預你,是否會對你自由權利構成侵害?第二,差別原則與機會均等原則事實上是基於已有社會等級體系提出來的。也就是説,它并不是基於平等主義的真空進行政治設計,而是基於承認社會現狀是由差異構成的。這個“差異”并不只是指你與鄰居不同,也指社會階層差異。比如李嘉誠與自營雜貨店店主就存在階層差異,就算政策傾向於雜貨店老闆并且他享有同等競爭機會,李嘉誠在現有社會等級中所掌握的話語權跟影響力,仍然可能促成不平等的社會關係。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哲學家 Niko Kolodny 針對 John Rawls 遺留下來的問題,提出了新方案,其主張可以視爲是進一步細化 John Rawls 的自由和平等原則:其一,在擁有能夠改善自身生活的機會時,人才是自由的;其二,人的自由不應該受到侵犯,不論這種侵犯是不是以“爲你好”的理由做出來的;其三,人的平等權利指人不應在社會等級體系中被置於“從屬”(inferiority)位置。
用作者自己的概括來説就是;要求改善的訴求(claims to improvement)、不受侵犯的權利(rigths against invasion)和要求不被置於從屬位置的訴求(claims against inferiority)。
在 Niko Kolodny 看來,人的政治審度,與其説是受自由驅動的,不如説是受從屬(inferiority)驅動的。然而,所謂“claims against inferiority”并不是要反對從屬關係本身(而且也不可能),而是要行爲人(在主觀或客觀上)避免涉及從屬關係的行爲。在行爲人是國家的時候,要求不被置於從屬位置的訴求,就是要求國家避免或不可造成權力和權威出現不受制約的不對稱性(untempered asymmetries),防止或者消除不受制約且不應該的懸殊差異(untempered, unmerited disparities in regard)。
Niko Kolodny 之所以特別在乎“從屬”問題,是因爲國家與個人處於極不對稱的等級關係中。國家是已經確定的社會結構,個體與國家的關係在持續發展。國家可以觸及的範圍和領域非常廣汎,不但涵蓋社會的角角落落,還可能持續伸張。再者,鮮有限制可制約國家對個人合法施加的影響和命令。尤其是個人要避免與國家發生以上關係,不但成本過高,還難度極大。而且國家的決議通常是終極決議:因爲國家始終處於社會等級最高位置,在國家之上再沒有可以申訴的地方。與此同時,先前談論公民權利平等時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你與他人在公平權利上的平等,主要是因爲你們與國家之間存在互動。也就是説,權利平等是通過互動來體現的,而互動是在社會階層和等級體系已經存在的環境中發生的,這就很難避免互動過程受到這些因素制約。
個體能夠做什麽呢?就作者列舉出來的案例來看,比如要求懲治腐敗、要求反對歧視、要求平等待遇、要求法治、要求同等自由權利、要求機會均等、要求治理貧困問題以及要求不受侵犯自由的干預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不論是“hierarchy”,還是“inferiority”,在 Niko Kolodny 的哲學體系中都與常規用法有不太一致的地方。Niko Kolodny 在强調社會等級的時候,這裏的等級并不是作爲一種等級制度,而是作爲一種由階層分化導致的現實;在用到“inferiority” 一詞時,主要用來指代在社會等級中處於從屬地位或不利位置的情況。
承認作爲一種社會現實的社會等級,并不是要加深等級鴻溝和凸顯等級的不公平之處,而是恰恰相反:個人在社會等級製造的巨大壓迫感面前被迫屈從,被迫犧牲自己的自由來達成妥協,這個問題是可以通過制度性保障申訴權利來解決的。也可以説,承認社會等級這一現實,是爲了解決由社會等級引發的不公。
Niko Kolodny 認爲,單純地聲索自由平等權利是抽象的,而要求不被置於從屬位置則是更加具體地解決社會等級體系可能對個體造成的不公,包括威脅到個體充分實踐自由權利。於是自由與平等權利的問題,被轉換成了解決個體在社會等級中可能被迫從屬和被迫讓渡權利的問題,也就是說,被置換成了解決從屬性關係問題。
但是從 Niko Kolodny 的描述來看,解決從屬性關係問題,重心被放在個體對反抗社會等級不合理之上,體現出一種由下而上的追索路徑,從國家層面通過制度性設計來對抗社會等級體系(也許更有效)卻沒有受到深入討論。另外,如果個體在糾正等級體系的過程中,因遭遇到巨大阻力和成本,主動屈從於社會現實的情況,他應該得到哪些制度性協助和補償呢?這些都是有待深入考察的問題。